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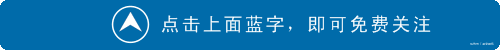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胡适(1891-1962年)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之一,也在“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学者认为,胡适“从1926年首次接触敦煌文书直到1962年告别人世,可以说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伴随了胡适大半生”(1)。至于胡适何时开始研究“敦煌学”,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1926年。当年,胡适趁赴英国开会之机,顺便调查研究过英藏、法藏敦煌 文文献。但实际上,胡适第一次研究敦煌文献的时间应该提前12年。早在1914年8月,胡适便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撰文,与英国汉学家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汉名翟来乐、翟林奈等,1875-1958年)讨论英藏敦煌汉文写本《敦煌录》。今天,在回顾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之际,有必要对胡适在“敦煌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评价,有必要对翟理斯在“敦煌学”史上的业绩进行回顾,也有必要对《敦煌录》的整理、研究历史进行总结。不过,本文限于篇幅,只是为了探索胡适与“敦煌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对胡适与翟理斯围绕《敦煌录》进行学术讨论的过程作一探讨。
【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一
《敦煌录》是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年)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获取的古代写本之一,1909年入藏大英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1973年转入英国国家图馆(The British Library)收藏。斯坦因最初为《敦煌录》确定的遗址编号是Ch.103号,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英博物院将其改编为S.5448号,沿用至今。《敦煌录》是一件册子装写本,正文共占14页,每页书写5行或6行,全文共898字。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文物于1909年初运抵英国偷敦大英博物院,在经过初步的整理、分类后,其中的汉文文献于1910年归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收藏。而当时该部主管汉文文献的管理员,便是翟理斯。
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汉学世家。其父赫尔伯特·阿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汉名翟李斯、翟理思等,1845—1935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汉学家,1897年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出生在中国,自幼随父亲学习汉语和汉学,于1900年进入大英博物院工作,负责管理汉文图书。1905年1910年间,翟理斯先后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论语》、《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2)
翟理斯从1910年开始研究敦煌汉文文献后,选中的第一件写本,便是《敦煌录》。经过几年研究之后,翟理斯在1914年7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4年卷第3期上,发表了他关于《敦煌录》的研究成果,题为《<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3),刊布了《敦煌录》全文的英译、考释、释文、照片等。这篇文章是翟理斯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敦煌录》也因此成为第一件被完全刊布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翟理斯在《<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的前言中说:
汉学研究在本国的衰败落后,通过一个事实便可已太过清晰地表现出来了。这个事实就是,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于5年前带回家的那批浩如烟海的汉文本当中,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部典籍,实际上是被刊布的第一部典籍。不过,有一件事不能说是完全不相宜的,那就是,这个光荣的地位,还是留给了一本简略记录敦煌地区的小册子,而且该小册子中还包括一段关于那些著名石窟的描述,整个写本搜集品就是发现于那些石窟中的。《敦煌录》的确有点简略,使人干着急,实际上总共才有893个字。但是,就在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它却触及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讨论,所需的空间要比这里能够提供给它们的空间大得多。最起码,一段话就可以为迄今从未被解决的棘手的地形测量学问题提供大量的线索。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它都值得一读,因为它是一篇短篇概述,总结了人们对唐朝末年这片地区所了解的一切,这片地区虽属遥远但却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将这篇典籍的断代确定在唐朝末年这一时期,其理由会在文中的附注中提供出来的。这件写本的书法粗陋,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清晰可辨的。不过,还是会发现有少数几个字,抄写者将它们写成了“草体”。这种字体对任何一位外国学者来说都是特别致命的绊脚石。我尽我最大的能力,解读了这些草字,但是由于缺少来自土著专家或其他专家的任何帮助,我还不能非常肯定地说,我的释读是否正确。至于文书的风格,简明扼要的程度往往使文意趋于朦胧不清,在某些段落里,是绝不容易提供断句标点的(如同在几乎所有汉文写本中一样,文中的断句标点是被省略掉的)。(4)
- 陆小曼当年到底有多美,连胡适都感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 赏美文|我的母亲(节选) 作者:胡适 诵读:王卉
- 胡适原声评论鲁迅,罕见!
- 胡适的孩子,一人出国留学,一人留在大陆,最后结局却大不相同
- 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胡适和江冬秀的爱情
- 徐志摩去世后,胡适说会为陆小曼负责,陆小曼为啥拒绝!
- 鲁迅和胡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 《觉醒年代》之黄侃:与胡适一生是冤家,离开北大后仍不放过胡
- 胡适与刘文典的友谊
- 胡适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他借出的钱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