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插图
《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
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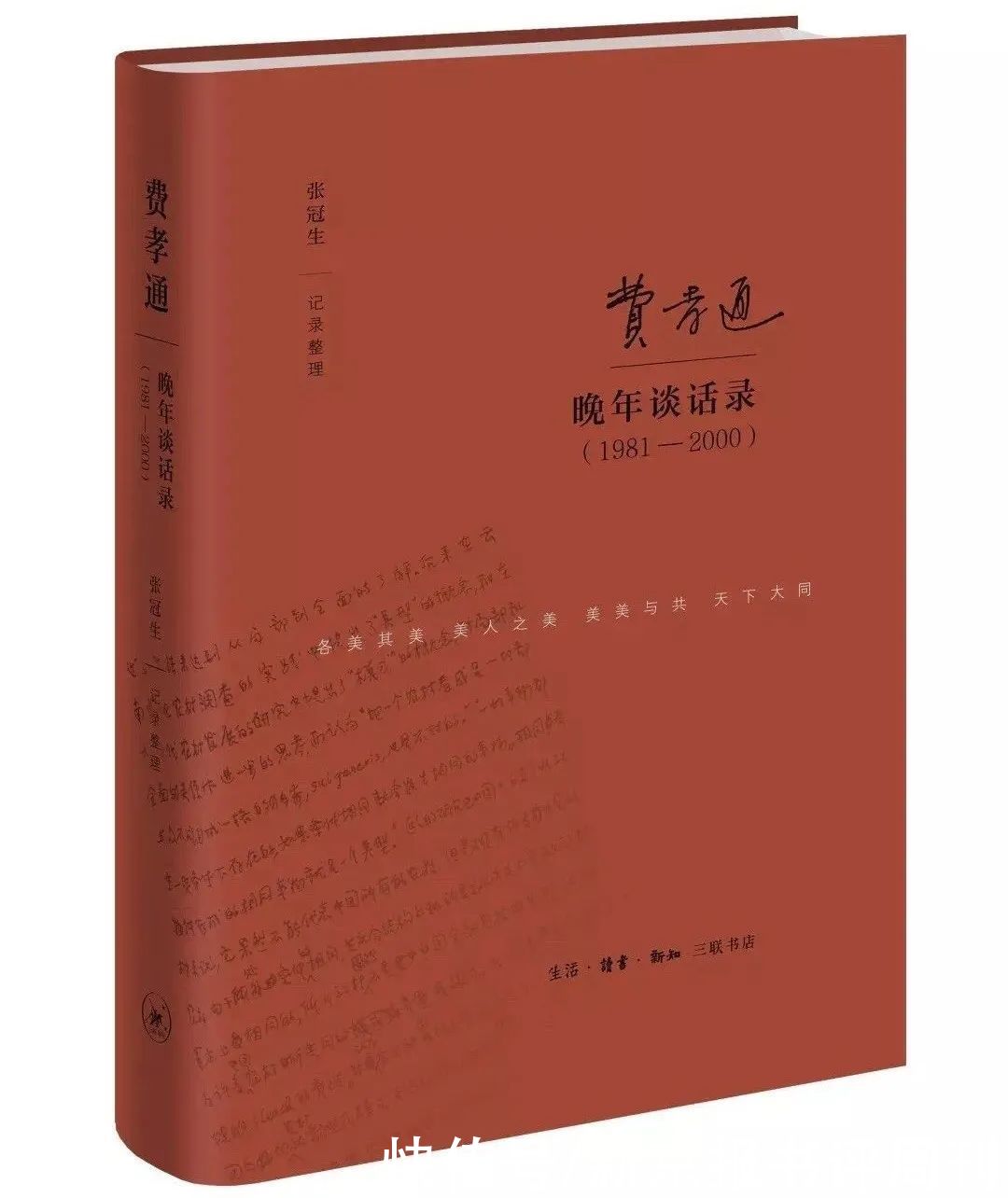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
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
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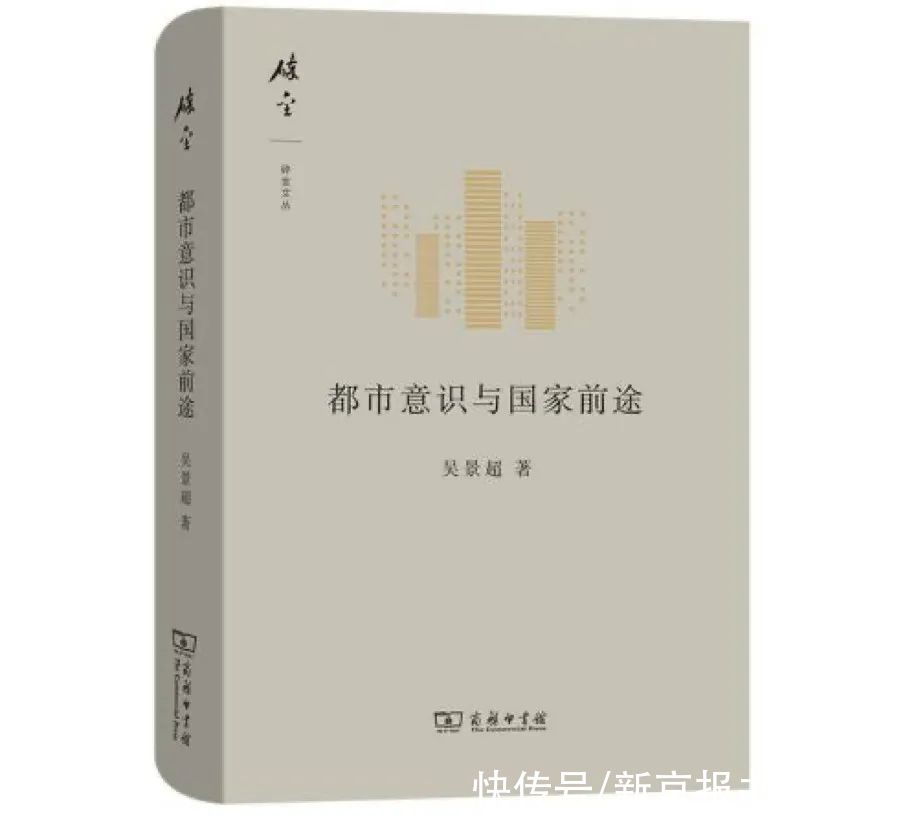
文章插图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
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
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
(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
- 历史文化专家潜心40年编撰千年古灵渠研究手稿发布
- 快赏齐白石书法
- 山东重特大科技攻关课题研究
- 近代诸子学研究的义理转向
- 为防泄密我军通讯说方言,国外专家窃听研究30天:讲的就不是中文
- 探寻俗文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 国内领先!洛阳建成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基地
- 此人位列五绝,但所有同级别高手都在研究对付他的武功
- 南艺举行2021届硕士研究生舞蹈毕业作品展演
-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救护组权威专家、北京呼吸疾病研究室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