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非常关注数学理论与定理,而很多定理都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不过,从来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定理最初是如何创立或发现的,对此我非常好奇。如此,我的两个兴趣点 —— “中国文化” 和 “数学” 便恰巧匹配在了一起。通过阅读两位资深法国学者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的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不只是我的幻想。可以说,科学史是隐形的,从高中教学内容中我们便可发现它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我先后攻读了数学硕士和数学史博士学位。在那时,这样的做法并不被鼓励,因为纯粹学数学看似更保险。但我并没有改变想法,与此同时,还开始进修汉学学位。很幸运的是,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了职位,于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进入CNRS 之前,我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这里(李约瑟研究所)进行研究。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科学史领域如此激动人心。那时,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楼上图书馆看书,意识到这个领域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和研究,并不只限于那些我曾经阅读过的中国数学典籍。自此,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
赵静一:您当时是先决定做汉学研究还是数学史研究呢?
詹嘉玲:我非常明白自己想要继续学习汉语。法国有一位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在他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972 年出版时,我正好开始学习汉语,父母将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我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所以当时根本无法阅读书中的文字。但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其中有一整页都是关于中国数学典籍的插图。由此,我开始知晓这个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我所好奇的问题是,数学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 “游历” 到另一个地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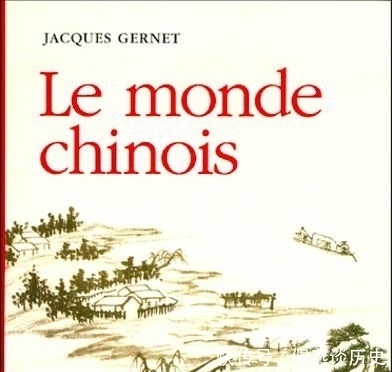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72 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内容与文化接触相关。后来,我接触到 17 世纪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我对这部作品有些许了解,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里学过的几何学非常有限,那时法国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集合论。
二、印象深刻的中国行
赵静一:说到学习中文,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曾经告诉我,有一次您参加学校组织的项目去台湾旅行,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由于阴差阳错你们的团队并没有老师陪同,是吗?
詹嘉玲:是的,我高中毕业后那个暑假,老师组织我们去台湾旅行。因为当时是 1978 年,对年轻学生来说,去中国大陆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领队老师错过了飞机,而我们则按计划到了香港。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恰巧也是中文最好的,于是我翻开电话簿给我们将要前往的香港大学的住所打电话。事实上,当时用英语是行得通的,而我没有多想,因为我一直接受的教育便是,说当地的语言是对那里的人表示尊重。
我十分紧张地用中文说了几句,但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有些脾气。我对同行伙伴们说,让我们直接去那儿吧。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在香港没有人说普通话,都是说粤语。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乘坐下一架班机抵达,她非常努力地说普通话,但这在香港根本行不通。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中文,但如你所知,没有什么比在电话中说外语更加困难的了,因为你无法用肢体语言来帮助你表达。如果你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很难理解你。
赵静一:您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是怎样的?
詹嘉玲: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 1981 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暑期班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在学习数学之余能够更好地提升我的汉语水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那次中国行,而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我感受到了在法国失去的、或者说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好客。那一年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专门教外国学生的老师,学校为我们分配到了一名平时给中国学生教中国文学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仲。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还与仲老师一起参观了许多景点,他为我们一路讲解。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中国行。
- 历史文化专家潜心40年编撰千年古灵渠研究手稿发布
- 快赏齐白石书法
- 山东重特大科技攻关课题研究
- 法国史学家笔下的宋徽宗
- 近代诸子学研究的义理转向
- 为防泄密我军通讯说方言,国外专家窃听研究30天:讲的就不是中文
- 独家专访|M/M(Paris):以设计与世界对话
- 探寻俗文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 国内领先!洛阳建成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基地
- 500年前的一把中国折扇,如何让一个意大利女人成为法国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