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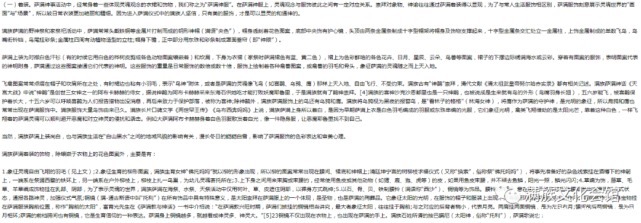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二、显灵:满族萨满仪式与审美的文化契合
萨满仪式是因解决灵魂走向和生活难题而进行的一种文化操作,里面涉及情感、期待、想象与审美;有大量的艺术或“半艺术”元素渗透在萨满仪式当中。凡是符合萨满信仰理念的,则被视为愉神的、悦人的,因而是美的;而违背萨满信仰的一切言行或作品,都被视为肮脏的、污染的、丑陋的。萨满仪式培育的满族的审美意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那些迄今仍然信奉萨满的部分满族的审美判断。
首先,基于对萨满仪式中的着装、神歌与咒语、情节性跳神的审美分析,满族萨满仪式上的巫术(法术)活动,可以看成是满族审美作品的集中展示。人们用自认为是美的东西,跟神灵交通。只要人们愿意用审美的眼光审视,满族萨满仪式中的一切准艺术、准审美的萨满法物,都可以看成是满族重要的民间艺术遗存。对于不熟悉巫术传统的群体而言,萨满法物和行为无所谓美丑;而对于满族而言,美的意识已经在萨满仪式中偷偷发生,并且带有强烈的族群和地域的面孔和审美评价。这可以用英国著名美学家科林伍德的说法来描述。科林伍德认为,巫术更接近艺术,它是一种“半艺术”:“巫术活动总是包含着舞蹈、歌唱、绘画或造型艺术等活动,并且不是作为边缘因素而是作为中心因素而存在于艺术中的。”[11]219
其次,满族的萨满艺术不脱萨满仪式,而萨满仪式在操作当中,歪打正着地循着审美的规则创造着。当左肩挂一面铜镜,右面也要挂一面,以便两端对称;祭“佛托妈妈”时,花索一端系在箭上,另一端就系在门上,也是追求对称的原则;再如,基于现实功利的审美,往往以对现实功利的超越为己任,这在萨满仪式的审美呈现中也是俯拾即是。满族萨满仪式表演既模拟现实(自然的模仿),又超越现实(神的模仿),仪式中的仿真不是真,是虚拟和象征,再造一个想象的世界(萨满“显现”的灵魂的世界)以便与现实世界加以区别,这一点很像艺术制作和表演,具有审美活动的一般特征。萨满信仰呈现出来的服饰披挂众多,有别于日常服饰;信仰的神明(萨满的灵魂)也要与常人有所不同(萨满教常将残疾人或奇石怪树等畸变形象作为萨满神灵或妖魔,如瘸腿的多霍洛瞒尼、驼背的布可他瞒爷等),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大萨满故事《乌布西奔妈妈》介绍童年时代的东海哑女乌布西奔像鸟一样聋哑,像海狸鼠那样呆傻,但她却是东海太阳神的女儿:
瘦羸的乌木林毕拉往昔像患有灾症,
部落间争吵不休,
瘟疫漫染,
葬尸抛满溪流。
阿布卡(天)惩戒不知是何缘由?
突然,
东海的清晨出现了两个太阳,
红光照彻了一个赤脚哑女,
招手能唤来白鹰成千,
招手能换来鲜鱼跃岸。
……
她用手语告谕罕王族众,
自称是东海太阳之女,
身领东海七百嘎珊萨满神位,
【 仪式中|满族萨满仪式的灵性审美探微】便可使乌布逊永世安宁。
……
如果不准领受萨满神主,
乌布逊老幼必遭罪咎!
无奈中,老罕王只得接受赤脚哑女的要求,
奉她为萨满神主。
傅英仁的《满族神话故事》中介绍珲春东海三十六部落中土伦部落的小阿哥突忽烈玛法,生来即与众不同,浑身长鳞片,双脚似鸭爪,生下三日即钻水不出,他被部落人坑害,只好夜深上岸回家吃饭直至15岁,大家仍想害死他,几个部落里的小阿哥挖了个坑,里面放着尖状石头欲加害他,突忽烈落坑后,其身上鳞片却将石锥碾碎,人们又用火烧他,反而练就了他不坏金身,后来他抗洪有功,拯救部落,被敬为神。这个鳞人鸭脚的奇人突忽烈,不禁让人想到《山海经》中披发戴胜、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变形想象,是神话-仪式思维的重要特征,也是宗教利用违反日常审美的一种惯常做法。
- 賈学新|弘扬满族文化的賈学新
- 民俗|满族舞蹈展现满族曾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 胤礽|胤禛抓周仪式上,拿着毛笔胡乱画了几下,康熙帝看后当场脸色骤变
- 上演|好节目轮番上演!珠海这场禁毒文艺大赛颁奖仪式真精彩
- 新网红打卡地 中街满族大院明天揭面纱
- 仪式|电视剧《父辈的战场》启动仪式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
- 满族刺绣|“娃衣”变新潮 满绣焕生机
- 颁奖仪式|中匈儿童画创作交流颁奖仪式在苏州市吴江区举行
- 书法字画|各界人士吊唁欧阳中石,告别仪式将于11日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 隋唐|日本天皇立储仪式,唐朝服装抢镜,有孩子为何还要立弟弟为皇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