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你对打破传统风格的爱尔兰作家,像弗兰·奥布莱恩,会有兴趣吗?
托宾:确实像你说到的,除了传统的悲伤主题之外,其实另外一个爱尔兰的写作传统是有这种喜剧的色彩在里面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弗兰·奥布莱恩,他的文字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而且是充满玩味性质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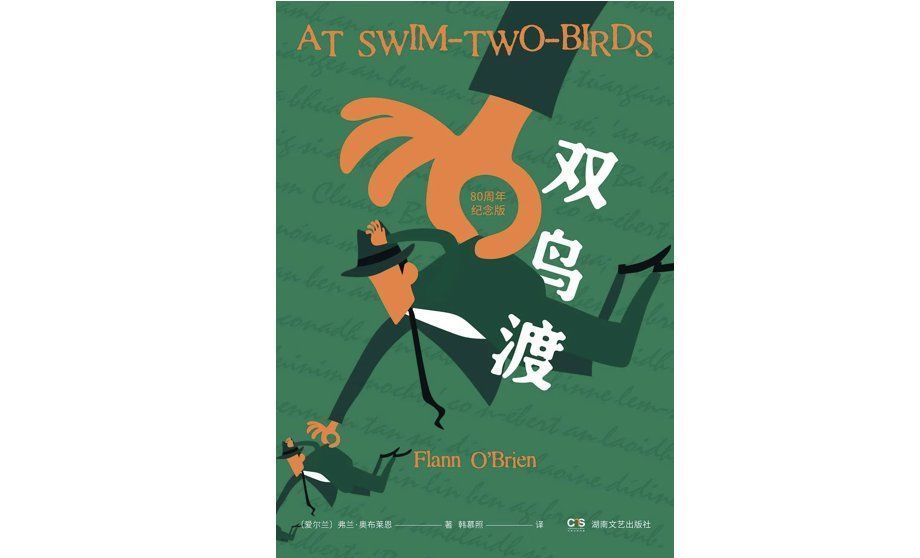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双鸟渡》,作者:(爱尔兰)弗兰·奥布莱恩,译者:韩慕照,版本:大鱼文库 |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
新京报:那萨莉·鲁尼呢,她的小说,我觉得读起来已经和爱尔兰没有什么关系了。
托宾:说到萨莉·鲁尼,其实我对于她的作品是非常欣赏的,她所描绘的都柏林恰恰是一种当下所发生的。她所描述的是这一年以及此时此刻的事情,对我来说她非常精准呈现了现在爱尔兰的日常。而且,其实在她的作品中,我也可以找到这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悲伤,这两点和你刚刚说的爱尔兰叙事传承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她写的东西,她所呈现的虽然是一种新的面貌,但是也是传统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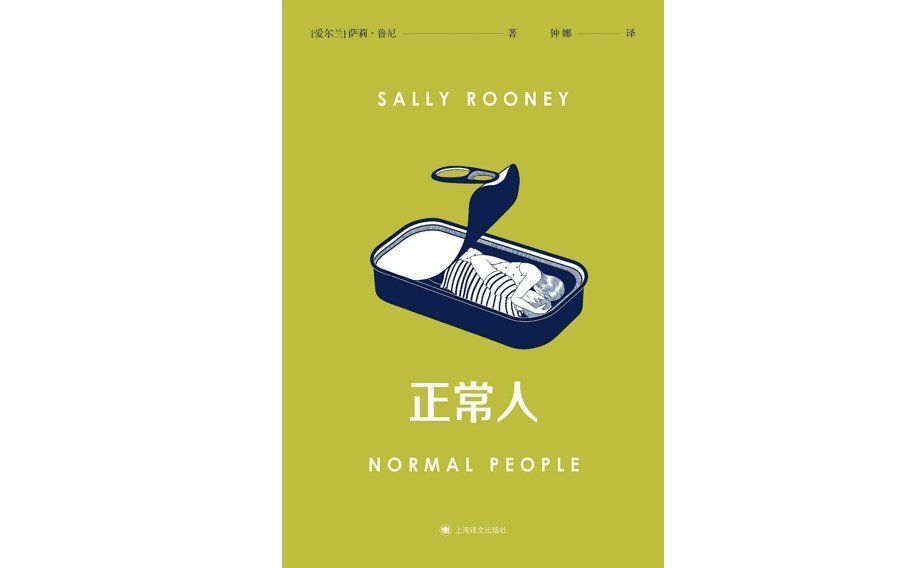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正常人》,作者:(爱尔兰)萨莉·鲁尼,译者:钟娜,版本:群岛图书 |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7月
来自都柏林的观察与许诺
新京报:关于爱尔兰传统,你在《走到世界尽头》这本书里提到了一句话,“都柏林可能是整个爱尔兰最不爱尔兰的城市”。这次回到都柏林,你还有这种感受吗?
托宾:其实这就要说到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因为当时说的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时候,当时的作家以及诗人,他们会有一个倾向,把西部爱尔兰理想化,因为西部有大片贫瘠的田地,大片的农村,保持了非常传统的爱尔兰的面貌。与此同时,都柏林在爱尔兰的东部,它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而且它直接面对着英国,也是英国统治下的首府,呈现的是一种非传统的爱尔兰的面貌,这个是我说那句话的背景。
新京报:那还会碰到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写到的那些人物和场景吗?
托宾:其实现在如果到都柏林去的话,还是多少可以找到《都柏林人》里面所描述的一些小元素。比如说一些小的酒馆还是跟书里描述的是一样的,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氛围。但那毕竟是12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都柏林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如果你现在去都柏林的话,你看到的会是萨莉·鲁尼笔下的都柏林。

文章插图
《都柏林人》,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译者:王逢振,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
新京报:现在爱尔兰的年轻人对文学的关注度是什么样的?我之前在youtube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在街头向爱尔兰年轻人提问——你们了解《尤利西斯》这本书吗?结果大部分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有人回答,尤利西斯听起来像是卢浮宫里的一幅油画。
托宾: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当下多少都是这种状况。因为现在吸引年轻人注意的东西太多了,年轻人总是看手机、发消息,或者是听歌,出门约会等等。大部头的书对于他们来说吸引力是比较小的。但是现在我每年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本科生,我会让本科生来阅读《尤利西斯》,令我挺惊讶的是,虽然我的这些学生没有去过爱尔兰,书也是一百多年前写的,书里所描绘的跟我学生的日常生活是这么不一样,但是我的学生可以迅速和人物产生共情,会很快搞清布卢姆是谁,史蒂夫是谁,而且了解书中描述的街道和城市里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例证吧,通过阅读,通过书籍,我们可以产生这种跨越国界线,跨越国家之间的这种连接。
但是也要说到,其实书籍并不像电影院里面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它的吸引力毕竟没有那么大。打个比方,如果你在街上手中拿着《尤利西斯》这本书,很难说会找到灵魂伴侣,不会有人走上前告诉你说,你也读这本书,我特别喜欢之类的。
新京报:那你有的时候会担心小说或者是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低,然后渐渐消亡吗?尤其在今天,大量的作家越来越关注像人工智能,女权主义,黑人运动,这些每个新闻头条都会关心的问题。如果不写这些的话,可能作品就得不到什么关注。
托宾:不,对我来说,我毫不担心小说的消亡。因为我始终觉得阅读是特别小众的爱好,当然当下会有很多作者,他们会紧跟形势描写当下的议题,比方说人工智能等等,会有一些人写到关于科技或者技术等等。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写不来这样的题材,而且我也不担心有这样的消亡。
- 周易|让日常生活美起来|隐于市的“江湖人”,午休一小时仗剑走天涯
- 欢团|晨读 | 欢团圆子
- 低谷时,帮你破局的三把钥匙|哲思 | 触底反弹
- 石器时代|首次确认!金沙江岩画是东亚最古老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
- 行业|年份酒的“年份”是个谜?白酒产业将迎“真年份”时代
- 小软饼|时蔬土豆小软饼
- 辅食油|番茄时蔬鸡肉小丸子
- 番茄酱|番茄牛肉汤
- 齐刀币|山东淄博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 快时代里的“慢美学”,二十四节气藏着中国智慧|文化时评 | 二十四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