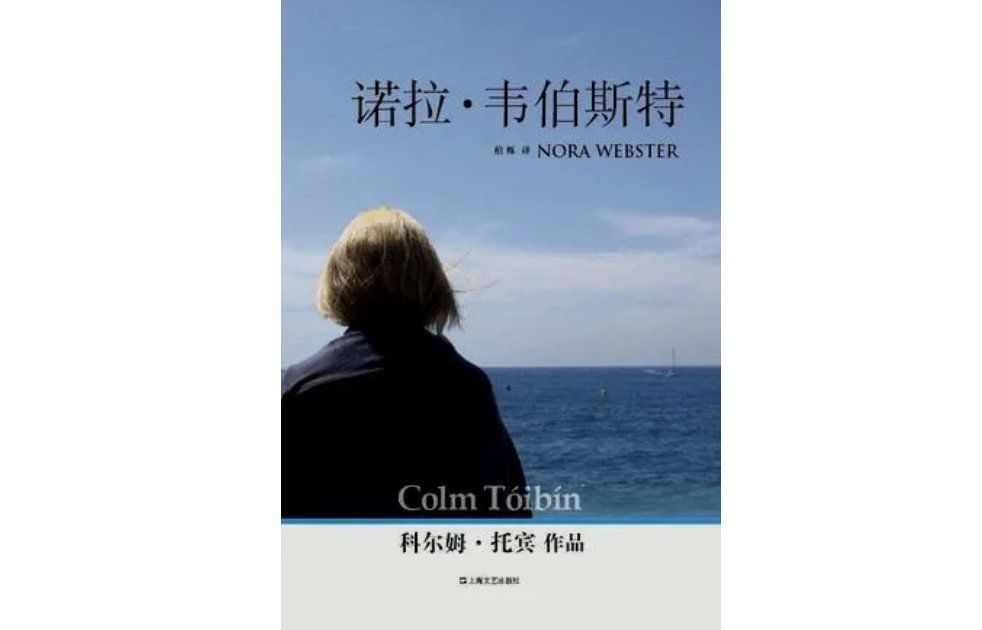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诺拉·韦伯斯特》,作者:科尔姆·托宾,译者:柏栎,版本:99读书人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
新京报:大概一篇小说会修改几遍?
托宾:对我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复阅读的过程,比方当你写完一个句子以后你会重读它,读完之后你会觉得有些地方我需要做补充,这个句子应该承上启下等等,你会相应的做一些修改。你在写了几页之后,也会再重读它,读完之后可能觉得需要改,需要重写。其实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你需要全身心不断用审视的眼光做出判断的过程。有的时候这个修改时间比较短,有的时候耗时更长。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写作跟游泳、跑步还有其他运动一样,是找到呼吸的节奏。当节奏呼吸很顺的时候,写得也很顺。但是这个节奏如果卡顿了,那么写的时候可能也没那么顺利。
新京报:这种写作的节奏感,你觉得是能够后天培养形成的吗?
托宾:其实我觉得写作这个事情就跟唱歌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跑调或者是音痴之类的,就是没法唱歌,唱不了。写作也是如此,如果有的人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那么其实这样的作品是可以有所提高的。因为在写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这个意识,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在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是没有学过的,也没有人教过我,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我觉得写作这个事情只能说是人各有才吧,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才华。
新京报:你会和创意写作课的学生们直说这一点吗——“算了吧,你就不适合写作”。
托宾:哈哈哈,不,我是个善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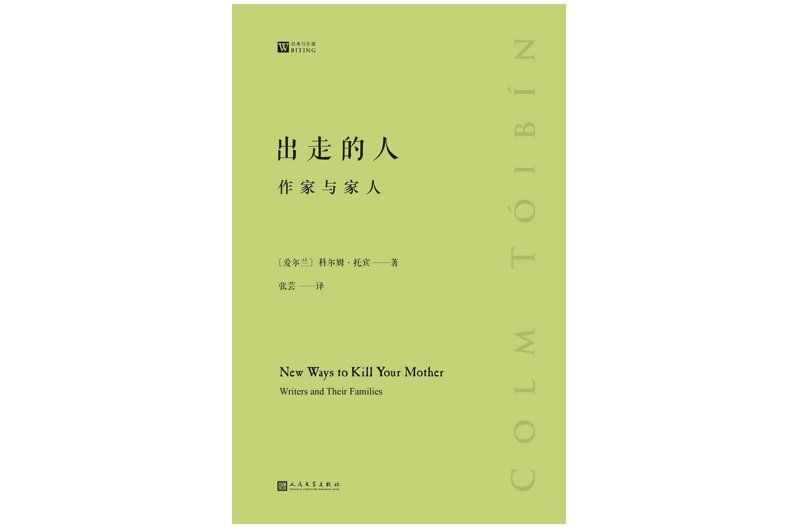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出走的人》,作者:科尔姆·托宾,译者:张芸,版本: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写作与阅读都应像随时起飞的鸟
新京报:我想说一下你的另一本书《黑暗时代的爱》,这本书提到,卡夫卡可能是一个同性恋作家。这个我是很不赞同的。而且即使从性别视角出发,卡夫卡可以是柏拉图主义者,也可以是无性恋,这些好像也更符合他人物作品当中的心境。
托宾:你说到序言里面的引用,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而且挺复杂的。首先说一下你刚刚引用的那一段。这一段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卡夫卡的人物,看起来由于他们的各种压抑,受到的压制,以及他们在家庭所受到的对待等等,让他们的情感和情绪等方面,以及他们的境遇,与同性恋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如果想要将卡夫卡和他的人物解读为同性恋的话,是说得通的。但是确实如你所说,人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如果带着一个预设的想法去读的话,肯定没有那么正确的,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卡夫卡,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作者,所以他写出来的人物或者是内容会呈现出某种情况。
才会明白他所有主人公的困境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卡夫卡毕生都在可以隐瞒他的性取向,他在私信、日记、笔记或是创作性作品中有些许流露,这也毫不奇怪……——鲁斯·蒂芬布伦纳

文章插图
《黑暗时代的爱》,作者:科尔姆·托宾,译者:柏栎,版本: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
新京报:因为我在想,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会带来封闭性的问题。比如说只有同性恋读者可以理解同性恋作家的小说,或者只有黑人能够最正确地理解黑人的作品。
我记得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是去年布克奖的时候,有一个入围的作家叫布兰顿·泰勒。他的观点比较极端,比如认为只有黑人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他永远不为白人写作。

文章插图
布兰顿·泰勒。
托宾:其实我也读过你刚刚读过的布兰顿·泰勒所做的一些表述,我觉得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黑人作家,他没有写黑人的故事向白人读者去证明或者是解释的义务,这不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或者是工作。说到黑人的作家,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也说过,他的读者可能首先是黑人读者,之后会有其他的读者。
所以我觉得书和想象力都不应该是封闭的,书和想象力都像鸟一样——鸟在飞行的时候是不知道边界在哪里的,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一个国家越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边界线。我觉得我们在阅读时候也应该这样阅读来自各个地方的文字。
- 周易|让日常生活美起来|隐于市的“江湖人”,午休一小时仗剑走天涯
- 欢团|晨读 | 欢团圆子
- 低谷时,帮你破局的三把钥匙|哲思 | 触底反弹
- 石器时代|首次确认!金沙江岩画是东亚最古老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
- 行业|年份酒的“年份”是个谜?白酒产业将迎“真年份”时代
- 小软饼|时蔬土豆小软饼
- 辅食油|番茄时蔬鸡肉小丸子
- 番茄酱|番茄牛肉汤
- 齐刀币|山东淄博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 快时代里的“慢美学”,二十四节气藏着中国智慧|文化时评 | 二十四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