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互联网摸鱼大赏( 二 )
劳动者觉得他们获得的报酬是「获利」,因而偶尔摸鱼成为一种隐秘的怠工,仿佛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内卷者看来,这种摸鱼无疑是可耻的。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工作已经超越情感和生活成为压力最大的来源。脉脉《向内而生:中国职场流动趋势年度报告2020》中,71%的人称工作是让自己产生焦虑的最主要因素,高达第一。

文章插图
《2020企业健康福利洞察报告》也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25-30岁以下的职场人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因处于事业上升瓶颈期状态迷茫焦虑,压力值高达7.4,成为职场压力最高的群体。而25岁以下的职场青年,也因为收入减少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经济上“腹背受敌”,压力值稍低排行第二为7.2。
事实情况是,人们需要摸鱼,这像是一种情感补偿机制。面对高压而无法挣脱的工作时,雇员需要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与自我达成和解,从情感上对自己形成保护。
像此前热议的「清华大学摸鱼学导论」事件,该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也认为,他在摸鱼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尝试,「摸鱼并不意味着不想努力」,而是学生在高压下的调侃和自嘲,是释放压力的出口。
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摸鱼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虽然自己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技术的进步让生产性工作大量减少,但劳动者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无暇追求他们想要的快乐。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话已至此,内卷达人大可不必对摸鱼人指指点点。《Gallup全球职场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不摸鱼的员工在142个国家中的占比不到15%。所以说,摸鱼人才是正道。
03
知识民工的觉醒
彭凯平的评价其实还有后半句,“这是一种反抗,一种辛酸,一种正义。”
不仅是学生群体,在最早提出「996.ICU」的重灾区互联网,「摸鱼」语义的背后,才是更广泛的程序员群体对当下剥削工作制度的挑战,它和「IT民工、打工人、码农」等词语一样,是现代社会某种群体的集体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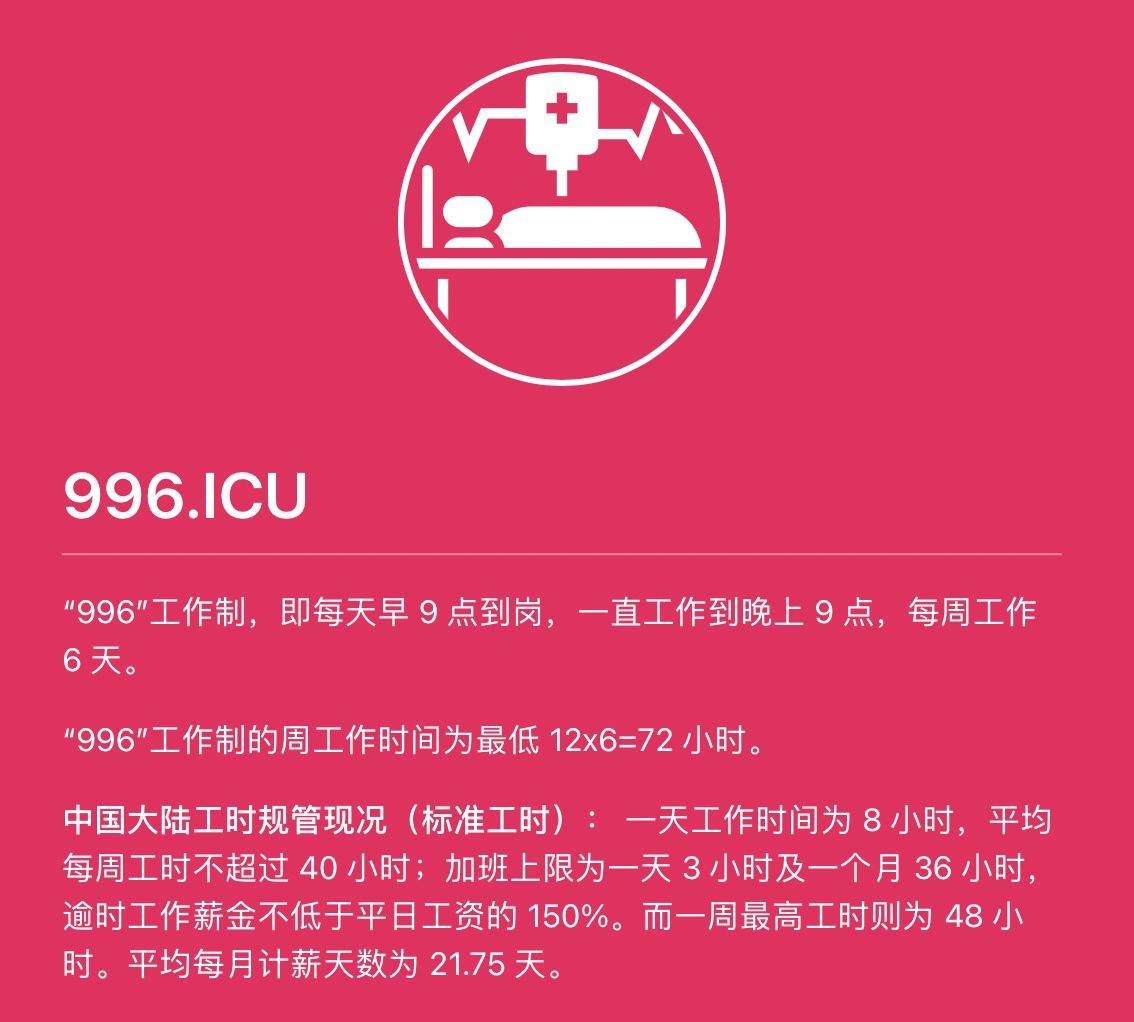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资本家和工厂主当然会厌恶类似「摸鱼」的表达和行为,甚至上升到「夜里暗抠Alt键」这种矫正。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这群知识民工已经压力大到开始用摸鱼来自我排解时,这不仅是一种情绪撒娇和缓解,而是隐藏了某种统一化、规模化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比如「非暴力不合作」的罢工,比如「假装配合」的摸鱼上班。这样的劳动者意识觉醒必然会影响大企业剥削剩余价值和加速资本累积的进程。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企业主觉得「打工的不如以前不好管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起源于工业机器化生产时期的企业的管理策略主要有两种,「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直接控制是指企业通过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设计让技术工作从工人群体剥离,并集中于管理层,这就让机器制造业的大批工人沦为去技术化的体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劳动者逐渐成为「在指令下重复劳动的新型机器」;责任自治认为技术不可能完全从劳动中剥离,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权或者说自主性。
但现代企业并没有因此完全进化,他们经常会设置一种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比如人们认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战的程序员群体,由于编程工作的创造性他们本该在劳动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但企业通过一系列生产规则、标准和微观劳动流程的设计,让这群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者的工作也变得单一乏味。
学者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型劳动者」,但其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而当这些涉及OKR、KPI等绩效考核的目标被分配到劳动者头上时,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知识民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耻感」,这种「耻感」加剧了他们的加班。
但这种加班不是自发主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意」,是被迫的过程。学者布洛维认为,在责任自治中,企业擅长运用一系列规则、标准和流程干预,让劳动者全身心投入这场「赶工游戏」,从未忽略了雇佣关系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质。换言之,看上去是劳动者自发在加班,但实际上还是管理策略在发挥作用。
- 互联网|传统企业里,产品经理的价值衡量难题
- type-c|互联网公司纷纷裁员,寒冬真的来了吗?
- hr|互联网企业监控员工上班引热议,是时候关注员工体验了?!
- |国内互联网巨头风向变了
- 显卡|互联网大厂,裁员消息频频出现,背后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现象?
- 贵州网新闻|让中专生圆梦!传智互联网学校科学解决人才“供需矛盾”
- 裁员|知乎被曝大裁员、B站审核员猝死、后台监测员工跳槽,互联网就业者的人生百态!
- OPPO Find|摸鱼办公两不误!集合高效与便携,工作人士入手Find N就对了
- 中国互联|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加班这么严重还是干不过老美?
- 互联网创业|考察互联网创业项目的几个核心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