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习惯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儿子安静地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后来开始学着应对他在国外,尤其是东亚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在首尔,他曾在一个室外体育场向1.4 万人演讲;在东京,他的演讲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500美元一张。在中国,他激发了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他在这里成为明星般的人物。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护照检查官拦住他,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
在厦门大学的报告厅外面,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最后主办方决定将门打开,以便更好地维持秩序。因此,尽管有消防法规,他们还是让人群涌入过道,密密麻麻的年轻人坐满了每一个角落。
桑德尔走上讲台,在他身后是一块巨大的塑料横幅,写着他新书的名字:《金钱不能买什么》。在这本书中,他询问道,是不是现代生活的很多特征,正在变成他所说的“牟利的工具”。在中国,钟摆已经迅速地远离了计划经济,如今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有一个价签:服兵役、幼儿园上学资格、法官的裁决等等。桑德尔所传递的信息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听众全神贯注。他告诉听众:“我并不是在反对市场本身;我是在说,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变成了市场社会。”
桑德尔提到了从报纸头条上读来的一个故事:某个来自安徽省一个贫困地区的高中生将自己的肾卖了3500美元;当他拿着iPad和iPhone回到家之后,他的母亲发现了这场交易;紧接着他出现了肾衰竭。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另外8人随后被捕——他们已经以10倍的价格把这颗肾转卖了出去。“中国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桑德尔告诉听众,“不过,每年只有1万个可用的器官。”他接着发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支持合法地通过自由市场来买卖肾器官呢?”
一个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国年轻人,身穿一件白色运动衫,戴着厚厚的眼镜,举起手表达了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认为使肾器官交易合法化会消除黑市。其他人则不同意他的观点。桑德尔突然加大了砝码,假设一个中国父亲先是卖了一颗肾,“几年后,他又要送老二上学,这时一个人来问他,如果他愿意放弃生命的话,是不是愿意把另一颗肾(或心脏)也卖了。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彼得想了想,说:“只要是自由、透明、公开的,富人就可以买到生命,这不是不道德的。”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男子喊道:“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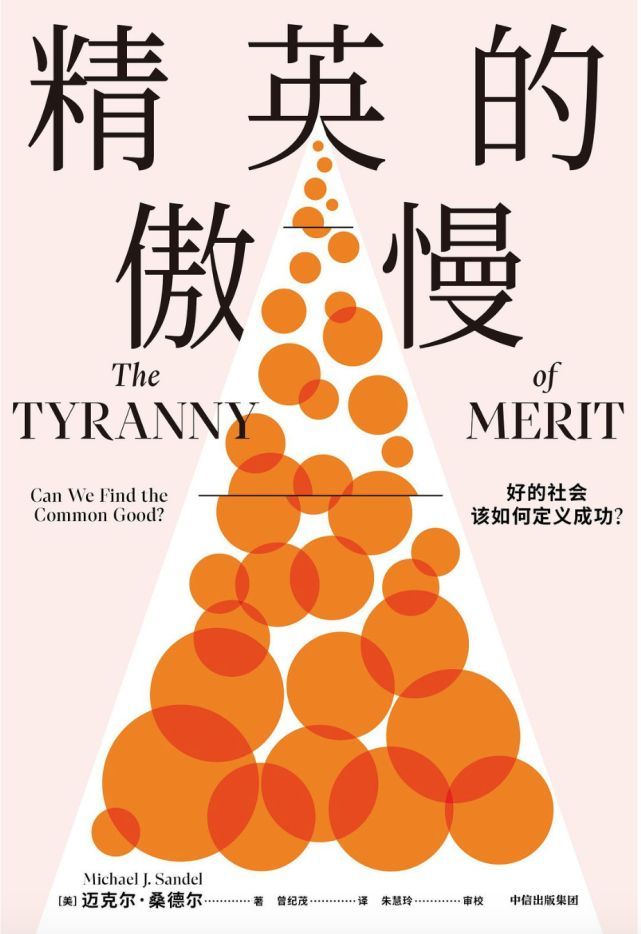
文章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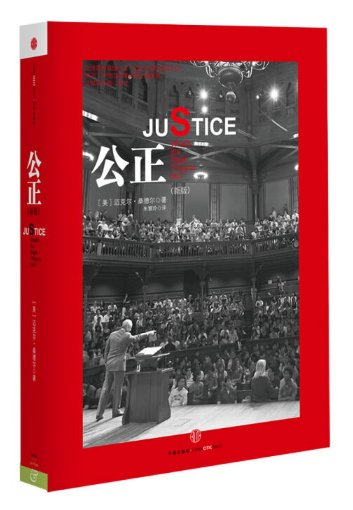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桑德尔已出版作品
桑德尔让现场安静下来,接着问:“市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想要如何一起生活的问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买卖的社会吗?”
第二天,桑德尔告诉我:“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都是最深刻的。”不过,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与此相对的力量,也就是从人群中传来的对卖第二颗肾感到不安的声音。他说:“如果你通过讨论进一步探究并考察这些直觉,就会发现他们在道德上犹豫要不要将市场逻辑延伸至每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观众一般会接受黄牛票——高价转卖演唱会门票,甚至是公立医院看医生的号。但当我问他们,在春节人人都要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允许黄牛倒卖火车票,大多数人表示反对。”
在中国,外国思想引发公众关注和学术讨论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一战”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封闭的,但它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到访。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告诉我:“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来中国访问,除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和杜威的学生胡适,引荐了他们。”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引荐,杜威和另外几位学者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后来,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2007年,桑德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观众已经不再会因为一位西方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万分,因而互动就需要更加深入,而不仅仅是依靠好奇。汪晖说:“在桑德尔来中国之前,已经有好多西方学者来过了。一些哲学家,像罗尔斯及其正义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知识分子接受桑德尔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和协商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好事儿。”进行深入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介绍桑德尔的时候说,中国有着一颗“急迫的心”。
- 华佗|张仲景在华夏百位名人榜单上排第15位,他后人都有谁,现在都干啥
- 叙述者|疼痛不是生活的全部
- 西天取经|孙悟空打死的6个强盗,把他们的名字串起来,你会发现如来的秘密
- 筋斗云|孙悟空为何打死六个凡人?把他们的名字连一起,你会发现一个秘密
- 礼法|在汉朝的时候,不是这个年轻人坚持原则,菱角差点成了祭祀的主角
- 奥林匹克|孙小学子首批寒假作品来了!为他们点赞!
- 志愿服务活动|“文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 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华林坪社区
- 南海一号|南海发现800年前沉船,我国出资5亿打捞,英国一口咬定是他们的
- 佛像|他是如来佛祖,因扮相太真遭路人跪拜,买佛像发现上面都是自己
- 北市|朱熹问学生:为何叫“买东西”不是“买南北”?10岁小孩一语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