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青未了丨风吹过檐头的青瓦( 二 )
熬过漫漫寒冬,青瓦又迎来一个煦暖的春天。一粒种子在瓦片的夹缝里,经雨水的浸润,开始萌发了。小小的草叶在风力摇摆着。阳光,空气,蓝天。它好奇地远眺,田野已经呈现盎然生机,麦苗喝足了春灌的河水,欢叫着分蘖,拔节。农民们忙碌起来了。弓着身子在麦田里除草、施肥。眼里茂密的麦苗,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片金黄的麦浪,心里美滋滋的,脸上有了笑意。鸡们也不甘寂寞,探头探脑走出村庄,在草地上啄食昆虫。几只啃草的山羊,偶尔朝着远方咩咩叫两声,像碧天上飘着的云朵。空气里鼓荡着一股躁动的生机,几只灰喜鹊滑过树梢,嘎的一声,停在屋檐上的青瓦上小憩。小朋友在河滩上采野花攥在手里的,有金黄的蒲公英、白色的苦菜花、星星般闪烁的荠菜花……家养的黄狗在草地上打完滚,舔着嫩草尖儿尝鲜味儿。田间小路上,扛着锄头的农人嘴角叼着一根旱烟卷,飞鸟归巢,牛羊下来,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母亲从青纱帐里钻出来,扛起农具,微凉的露水打湿了衣衫,风一吹,更觉得凉爽。她抬头看一眼,大而圆的月亮,照亮田野无边的生气。树木挺立在路边,茂密的叶子,竖起耳朵聆听从黄昏滑向黑夜的静谧。小路泛着白,弯曲着指向家的方向,母亲走过,脚印在寂静里敲打着沉重的叹息。一道道清白的炊烟,幽幽地上升,氤氲在青瓦的村庄之上。檐头的草,看着看着就迷失了自我。各家的煤油灯亮起来。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玉米面窝头在筐里堆起了尖,腌萝卜咸菜滴了几滴香油,金黄的玉米粥冒着热气。月亮慢慢升起来,青瓦上撒了一层白霜。村庄,披着夜色,洇染成一幅浓淡相间的水墨画。树木蘸了浓墨,点染了一片醉人的梦境。雾气笼着的青纱帐,飘飘然滑进更深的沉默里。深不可测的静,拨不开,扯不破。老牛一声哞叫,划过寂静的水面,仿佛一道深深的痕,像铁犁犁开大地的胸膛,倏尔又淹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年之中,乡亲们与瓦屋最亲近的季节是漫长的冬季。夏季,农人们早春晚归,田地里总有忙不完的庄稼活。春耕,秋收,也是紧张又繁忙的时候。唯有冬天,天寒地冻,田野袒露着胸膛,吹着凛冽的风。大人孩子便不出屋门,团聚在瓦屋的小火炉边,男人们喝几口小酒,女人们一直在纳鞋底,孩子们跑来跑去。瓦在屋顶上对抗着西北风,呵护着一家人的幸福安康。我喜欢听广播,在没有书读的日子里,一根青藤响万家,村子里的有线喇叭,在每家的屋檐下钻进屋子里,每个黄昏,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屋门后,支起耳朵,静心聆听。从维熙的《北国草》,路遥的《人生》等长篇小说,就是以这种方式听到的。没有人引导我,我自发地爱上了它,开启了我的文学梦。它让我知道,村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那里有境遇不同的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挣扎,成长。它让我明白,人生会经历酸甜苦辣,但不管在怎样的困境中,都得走下去。就像这屋顶上的瓦,经受一切的风雨的侵蚀,最终毅然牢牢地贴紧屋顶,完成生命的使命。
这些体验是融进村里每个人血液里的。青瓦在屋檐的高处,注视着世世代代的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青瓦的目光里,少年的我,在故乡的泥土里挣扎,以孱弱之躯对抗土地贫瘠与冷酷。爱恨交集,不得不承受这坚硬的疼痛,一直到十八岁我坐了长途车离开的那一天。岁月无情,把过往的一切抛掷。有些年轻人,像我一样“拔剑东门去,不顾归”,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走出故乡,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去求发展。多年之后,回望故乡,不由感慨良多。迷茫中的坚守,要抵制故乡的诱惑。父母的殷殷的期盼,同学恒久的情谊,甚至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在召唤着你。久居外乡,总念着故居上那些翘首盼归的青瓦,即使把他乡当故乡,也驱不走浸在骨髓里的孤独。远离村庄,远离那份幽深的梦境,仿佛躲不开青瓦的视线,它在岁月的深处凝望着我,抹不掉与它永久的牵绊。
多年之后,再回到故里,村庄已不再,那些青瓦早不知散落何处。
如今,像一部黑白默片,村庄的影像是一幅幅恍惚的画面,树木、房屋、小巷、乡人……时时在眼前晃动。那一种物象,虽然在现实中遁去身影,却已经深深地镌刻在生命的年轮里。
风中的青瓦,悠悠情思,一把二胡横空悠扬,无声处,声越寰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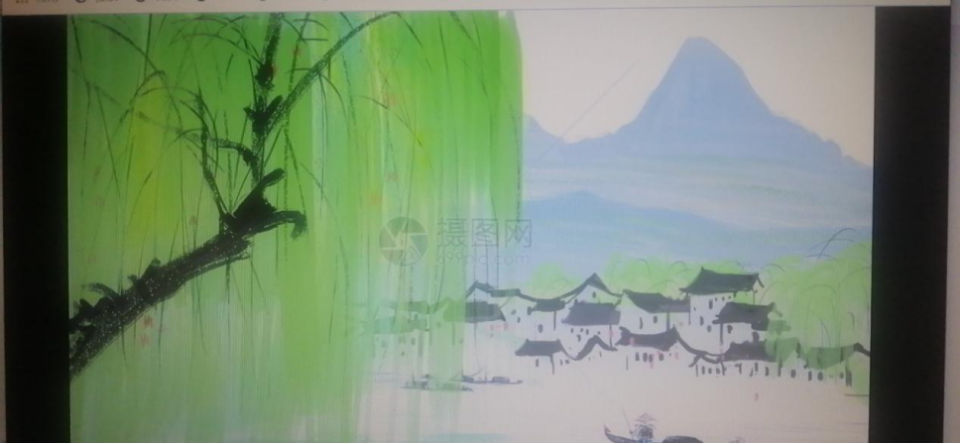
文章插图
作者:吕延梅,笔名绿叶子,山东散文学会会员,济宁市作协会员,新锐散文平台签约作家。多年来一直潜心散文创作,作品发表于《散文百家》《当代小说》《当代散文》《岁月》《聊城晚报》《济宁日报》等报刊杂志。
- 爷青回!魔兽第五种族Moon官宣中国开播,中国只有sky能与之比肩
- 追小麦返青肥用每斤硝态氮跟得上每斤尿素效果吗?答案来了
- 河北曲阳受央企国企青睐 总投资超300亿元项目集中签约
- 小姐姐牛仔裙搭配T恤,尽显青春气息
- 开门红!青岛市属企业经营效益首月同比增长12.7%
- 从广东足球名宿胡志军被学校,家长嫌弃,看中国足球青训之现状
- “综艺势力榜”王一博第一、张小斐第二,“青3”话题量破20亿
- 温柔甜美风的瑜伽裤,还透着微微的优雅温婉,绽放青春时代的魅力
- 舒适随意的连衣裙穿搭尽显青春朝气,简单搭配就足够美,休闲十足
- V领衬衫+皮质短裙,让街头美女展现“青春活力”,时尚又减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