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幽灵工作”:困在算法里的不止有外卖员( 三 )
在大部分的“幽灵工作”中,“无意识的算法残酷”指的是,有人建了一个系统,并将其中工作的“人”当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的设计剥夺了人的自主性权利,也将他们丢置于弱势的处境。
事实上,这些按需平台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把幽灵工人当作是真实的贡献者(contributor),而是假定他们会敷衍和欺骗客户。在这样的系统里,工人只要犯了极小的错误,就会面临被平台处罚甚至封禁的危险。由于平台对工人的管理是自动化的,他们在遇到劳务纠纷时,也没有任何申诉渠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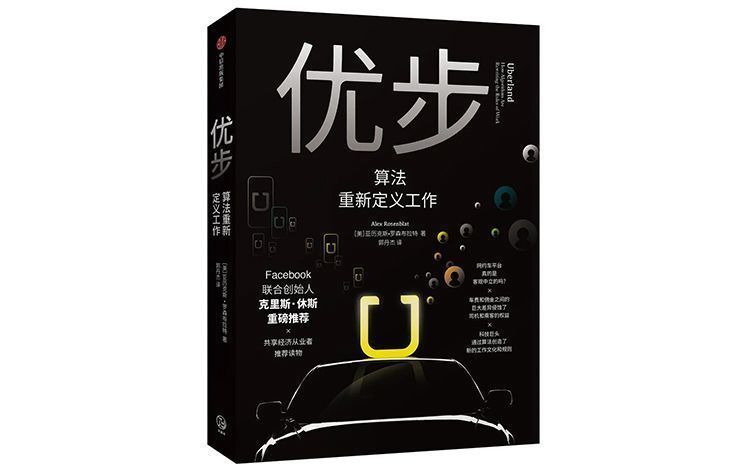
文章插图
《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作者: [美]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译者: 郭丹杰,版本: 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这和中国近期讨论的外卖员困在系统里很类似。
玛丽·L·格雷:是的,我也看了这则新闻。就拿外卖员事件举例子,类似“限时”这样的设定看起来是出于效率考量,但实际上是设计者否认了人可以自主评估形势并作出行动的基本能力。
保持人性化的关键因素就是承认人们有权利控制自己的时间。没有人是机器。因此,外卖员完全有权利参与制定送餐的时间表。剥夺这种权利就意味着,平台和消费者都认为,只要我们为此“支付了报酬”,就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基本生产权。
新京报:看起来,这种“无意识的算法残酷”也让幽灵工人无法获得这类工作本来宣称的灵活性。
玛丽·L·格雷:对。你说的是另一个面向。我们在研究中将其称之为“高度警觉”(hyper vigilance)。幽灵工作的确让很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来计划与安排工作。但对于想要借此谋生的人来说,他们必须不断在各个平台上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并追赶进度。那些赚钱最多的工人,每天需要花几个小时检查自己的数据面板浏览工作信息。像Mturk(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是亚马逊开发的在线劳工市场,“请求者”发布任务,工人通过领取与完成任务获得报酬。)这样的平台把工作的最低报酬设定为每项任务1美分,所以很多人必须翻完所有低价任务,才能找到相对体面的即时工作。
同时,幽灵工人群体内部也存在阶层差异。对于被迫依赖幽灵工作的低薪劳动者而言,他们往往需要同时兼顾多份幽灵工作,才能勉强维生。所谓掌控时间的灵活性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这些更为弱势的群体还面临劳动权益缺失的风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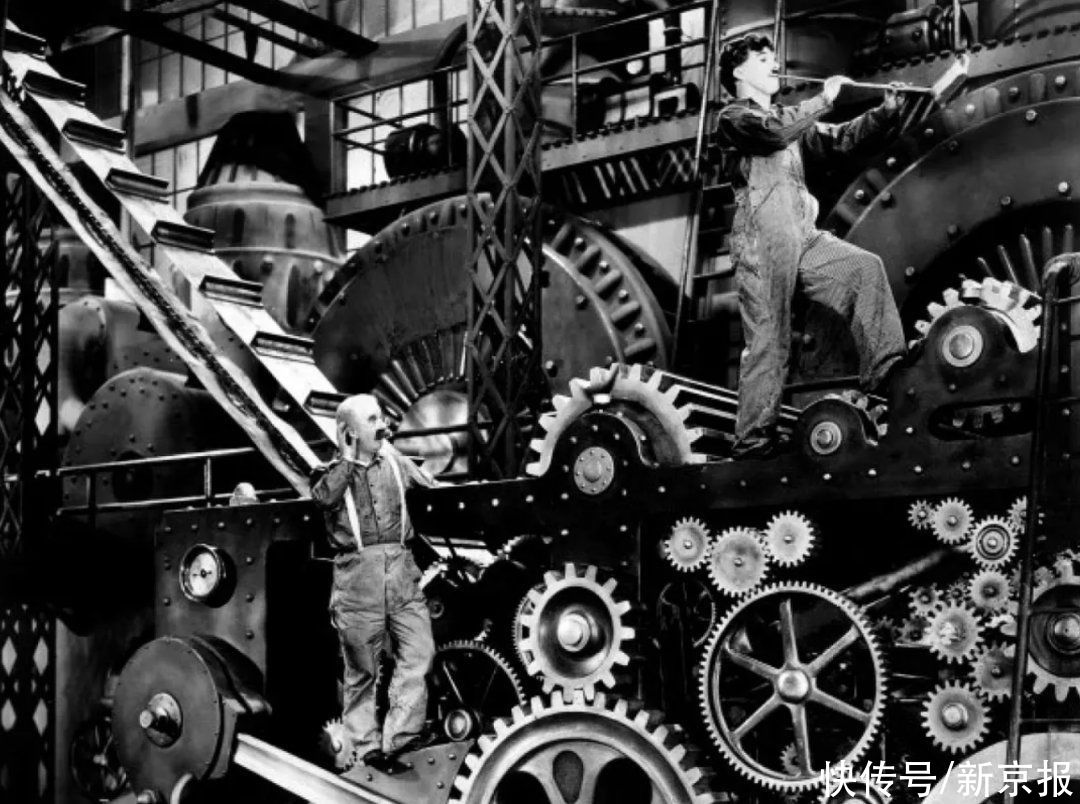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很多按需平台极力避免幽灵工人之间的协作。但不少工人还是自发联合起来,重建工作中的社交关系。你如何看待平台这种原子化的流程设计与工人自发的反抗行为?
玛丽·L·格雷:对。大部分幽灵工作平台的确是有意消除工人间的社交联结。他们认为,工人之间的社交是在浪费时间,还会影响工作效率。在他们看来,只有精准的匹配算法(注:匹配企业与幽灵工人)、原子化的工作以及自动/半自动化的管理才是高效的根本。
但实际上,工人间的互助与协作是数字经济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对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很大的帮助。协作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技术的缺陷的实际问题,也是他们重新感受到人性与善意的方式。借助社交网络,这些工人的协作不仅减少了他们的搜索与学习成本,同时,这种协作也让这份原子化的工作变得可持续。
新京报:你的另一个观点是,这种按需工作不一定是糟糕的零工。例如,它让许多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例如,残疾人,家庭妇女等)获得了工作机会。在某些时候,它也的确让一部分人可以围绕生活来安排工作。
玛丽·L·格雷:其实按需工作是好是坏,取决于它的设计以及背后的制度网络。在进一步判断它的好坏之前,我希望能够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情景加以审视,否则,这群工人就很可能被平台设计者隐藏在算法背后,成为真正看不见的“幽灵工作”。
另一方面,在我的研究里,任务制的按需工作的确给一部分人带来了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让它变得更可持续。毕竟,它很可能成为我们未来主要的工作形式。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至少在美国,8%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按需任务赚钱。也就是说,每100名处于工作年龄的美国人中,就有大约12人已经在从事某种形式的按需幽灵工作。从数据来看,我们更需要正视这样的劳动形式,让它从现在的糟糕处境中走出来。
- 小米科技|性价比拉满!TCL T8E-PRO QLED智屏当属潮玩世代的必备单品
- 华为鸿蒙系统|华为汽车战略布局,进入汽车行业的底气来自哪里?(车车佳)
- 浙江省|浙江的五大富豪,四位做过中国首富,仅马云的阿里就1年纳税366亿
- iOS|恒创科技:Linux日本云服务器安全设置的基本步骤
- javascript|手机移动端的PyTorch来了,还支持JavaScript
- 华为鸿蒙系统|鸿蒙是安卓“换皮”产品?一亿多用户,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 中关村|柳传志在这里被骗、掘金,书写半部科技史的中关村经历了什么?
- 彩电|彩电价格还跌吗?家电年底销售“小高潮”还会不会来?
- 手机维修|手机维修的猫腻‖你是不是上当了?
- 智能化|感知局限下,车路协同的“子弹”还得再飞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