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11月,贝多芬与那位他在信中称之为“永生的恋人”的女人经历了痛苦的离别。贝多芬研究权威梅纳德·所罗门令人信服的考证指出,这位“永生的恋人”就是与贝多芬过从甚密的布伦塔诺家族的安东妮·布伦塔诺夫人(她的妹妹、著名的才女贝蒂娜·布伦塔诺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女朋友,也是贝多芬艺术的崇拜者),这是贝多芬生命中唯一一位他爱过,同时也回应了他的爱情的女人。1823年,当贝多芬终于完成了这部“最伟大的钢琴作品”(布伦德尔语)时,他所题赠的对象正是安东妮·布伦塔诺夫人。迈入晚境的贝多芬在风烛残年之际,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错失徒劳而决绝地编织进一段又一段的变奏中,恰似一幅又一幅美丽的袖珍画(所罗门考证的关键物证之一正是贝多芬遗物中的两件象牙袖珍肖像)在他眼前一一出现又匆匆消逝,这些或长或短、或快或慢、或庄严或谐谑的变奏曲中包蕴着极为复杂而深刻的矛盾情感,一如所罗门的深刻洞见:“在这些变奏曲里这种极致不只一次在贝多芬音乐的范围内相遇:平庸与高尚在最逼仄的空间并列,莱波雷洛(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中之角色)在天体音响中间出现了,袖珍画与湿壁画融合为一。第19首的perpetuum mobile(无穷动)遭遇到第20首纯粹的平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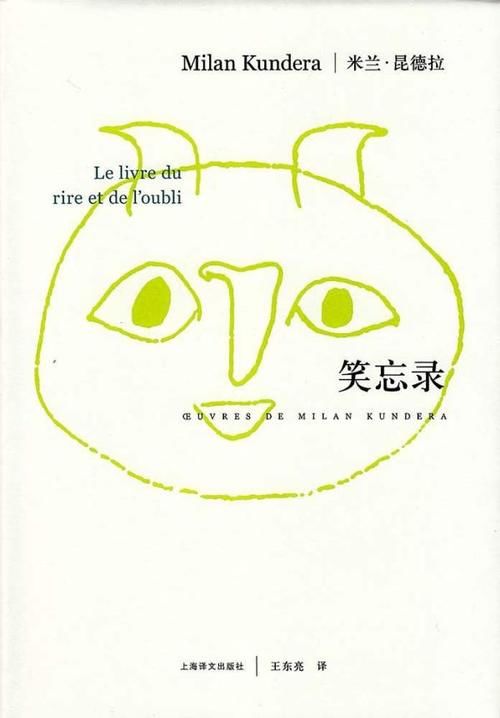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笑忘录》
1978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出版了小说《笑忘录》,根据他在书中的“夫子自道”:整个这本书就是变奏形式的一部小说。其实,昆德拉是用这部变奏曲式的小说来向他的父亲致敬——在他父亲离世前,他们所讨论的话题正是贝多芬《C小调钢琴奏鸣曲》(Op.111)的那个变奏曲终章。由此,昆德拉写道:“交响乐是音乐的史诗。可以说它像在广袤无际的外部世界穿越的一场旅行,从一处到另一处,越来越远。变奏曲也是一次旅行。但这一旅行并不是穿越在广袤无际的外部世界中。您一定知道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这样说过:人处在无限大的深渊和无限小的深渊之间。变奏曲的旅行把我们引入另一个无限之中,引入到隐藏在每一件事物里的内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之中”。是的,贝多芬用睥睨古今的九部交响曲完成了外部世界的伟大征程,而今回归内在世界的他以其天才的伟力成功实现了这一无限的转换——晚期作品中的变奏曲情结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的内在驱力,它以内心世界高度自由的遨游来抵御现实生命的残酷(尤其是错失生命中的至爱),从至为简单的十六个小节出发,去经历一场内在世界的宏大旅行和历险,他的每一个变奏都越来越与原始主题远离,原始主题与最后一个变奏的相像之处不比花朵与显微镜下花朵的影像的相像之处更多。在此,昆德拉终于憬悟了他父亲临终前的那句“现在我明白了!”,同时也打开了进入贝多芬晚期变奏曲圣殿的大门:
人知道自己不能够将宇宙及日月星辰揽入怀中,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错过另一个无限,近在身边的、伸手可及的无限。塔米娜错过了她无限的爱情,我错过了父亲,而每个人都错过些什么,因为要寻求完美,人们便深入到事物的内在世界之中,而这个内在世界是永远无法让人穷尽的。……盛年的贝多芬把变奏曲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形式,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像塔米娜和我一样清楚)的是,错过我们最爱的生命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贝多芬的最爱就是这十六个小节及其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内在世界。
晚年的贝多芬不时埋怨钢琴的局限性,甚至直到他最后的岁月,他仍对霍尔茨抱怨道:“它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台不能让人满意的乐器。”尽管如此,钢琴这个传递了贝多芬无限幻想、创造力和精湛技巧的最早的媒介,在形成他的晚期风格时,无可避免地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迪亚贝利变奏曲》是贝多芬以钢琴这一乐器的有限性去探索内在世界的无限可能性的最后一次伟大尝试,正如他之前在《E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9)和《C小调钢琴奏鸣曲》(Op.111)这两部晚期奏鸣曲中所做的那样,他将毕生的热情、回忆、幻想和技巧熔铸于其中,试图去抓住一些他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在此之前,他将《E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9)题赠给安东妮·布伦塔诺的女儿马克西米丽安),罗伯特·舒曼深情地将之称为“贝多芬用钢琴对听众的永别”。
- 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之中国书法
- 【非遗五进】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 世界遗产在德国系列(三)
- 舞蹈《绣女情》参加黄冈非物质文化遗产云上展演
- 《长宁车灯》正式出版
- 免费参观!历时4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试运行啦!
- 杜月笙去世,并没有给孟小冬留下遗产,那么她的经济是怎么来的
- 虚拟现实博物馆,让文化遗产代代流传
- 郭云深:身陷牢狱创拳法,一拳撂倒5大汉,后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 4岁时,母亲抛夫弃女去欧洲,病危她一眼都不看,死后收巨额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