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插图
梵乐希与波吉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巴黎教科文总部任国际公职人员时,法国常驻教科文代表团的团长是弗朗索瓦·瓦雷里,他的父亲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桂冠诗人”,名字被新月派译成“梵乐希”(Paul Valéry)。诗人闻一多追求其“节的匀称,句的均齐”,尤其受这位法国晚期象征派的影响,不免在自己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中有明显流露。曾经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盛成在港口城市塞特与梵乐希结识。1928年,盛成直接用法文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我的母亲》由维克多·阿丹热书局出版,梵乐希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从而跻身“东方学”领域。
我在巴黎拉丁区旧书店淘到一本《我的母亲》,读了这篇序言,并开始翻阅梵乐希的诗集《年轻的命运女神》等作品,探究他的“纯诗理论”,但好像总有些难求甚解。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于2006年刊印了《卡特琳·波吉与梵乐希通信集》,全书700余页,题为《火焰与灰烬》(La flamme et la cendre)。当时,笔者觉得书名蹊跷,更不知鸿雁传书人卡特琳·波吉为何方圣贤,竟然跟声名赫赫的梵氏有如此长久的通信史。况且,据出版社所称,这一册仅是“冰山一角”,二人绝大部分的书信都已依照波吉女士遗嘱,早已付之一炬了。
【 波吉|梵乐希与波吉的“八年孽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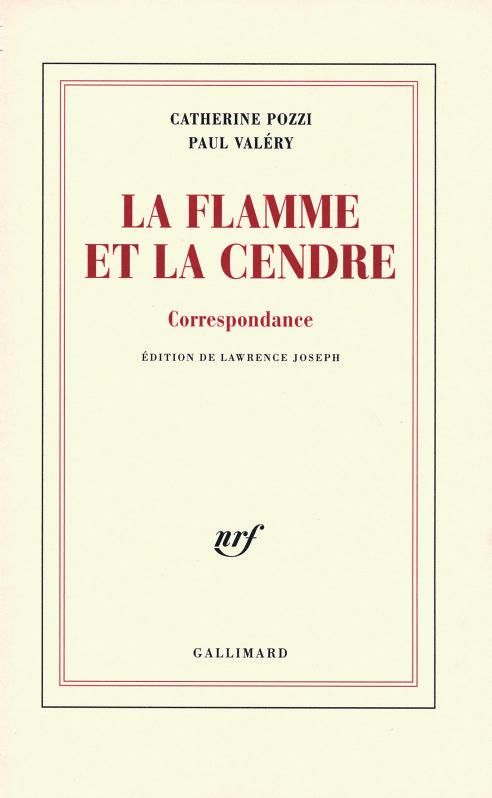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梵乐希与波吉书信集《火焰与灰烬》
事实上,梵乐希与波吉曾有过一段“八年孽缘”。波吉在去世前留言:“我要求遗嘱执行人当着证人的面,将保罗·梵乐希的亲笔信统统销毁,并告知他,为此心安。”此举显然是考虑到毁她一生的梵乐希的形象。获悉这一消息,梵乐希心知女方对自己耿耿于怀,在给他另一情人的信里承认,自己“松了一口气,祈愿把跟波吉的通信都烧光了事”。2003年,作家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在格拉塞出版社的“红色手册”系列丛书里发表《保罗·梵乐希的缪斯》,引用梵氏名言“当心情爱!”作者说:“可梵乐希本人并没能足够当心。他在家中接待过许多情妇。与他的担心正相反,这并没有损害他的文学创作”。米歇尔在书中列举了罗维拉男爵夫人和女雕塑家让娜·乐维顿等人,尤其是女作家卡特琳·波吉。他强调,这些见解高卓的女性向梵乐希提供了满足分析人欲所需的素材,从而使情感教育变为一种“作家培育过程”。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卡特琳·波吉(Catherine Pozzi,1882-1934),因为她身前身后都被梵乐希蓄意埋没,不见经传,最不为人所知。梵乐希的拥趸们甚至将她说成是个“歇斯底里”,根本不值一提的人。实际上,卡特琳·波吉心智极高,是一位颖悟非凡的作家和诗人。她出生在巴黎上流社会之家,10岁就开始写日记,在文学沙龙遇见高蹈派领袖勒贡特·德·里尔及其弟子约瑟-玛利亚·德·艾赫迪亚等诗苑秀士,受到精神贵族的文化熏陶。1909年她嫁给交易所经纪人兼剧作家艾德华·布赫岱,其子克洛德创办了极具影响的《观察家报》(l’Observateur)。卡特琳·波吉留有伴随她一生的符咒:“我感受,故我在。”2020年7月《影视综艺》周刊登载马利纳·朗德洛依的署名文章《焦灼的灵魂》,指出波吉精神的核心是主导心理的感受。他写道:“卡特琳·波吉跟保罗·梵乐希经历了毁灭性的情爱。梵乐希剽窃了她的独特见解,将她置于昏暗之中,应当承担女方本人遭受无法弥补的灾难之责。”
据朗德洛依披露,卡特琳·波吉是在巴黎闹市阿特奈大旅馆一次晚宴后跟梵乐希在一间卧房里约会的。初次见面,她就将自己构思的一整套哲理宣言和写作方案向对方和盘托出,其中涉及形而上学、基因遗传,乃至人类灵魂迹象的认知,引起梵乐希巨大兴趣。波吉尽管貌丑,人却内秀,且天资聪慧,梵乐希很快将其纳入了情妇之列。当时,梵乐希和波吉正巧都住在巴黎十六区,梵乐希在维勒鞠斯特街,波吉在隆尚街,密会去无多路。梵乐希常常一大早便来到波吉邸宅,二人相见恨晚,长谈不觉时移。梵乐希在写给其另一情妇让娜·乐维顿的信里承认,他与波吉罕见的酷烈关系里包含着妒嫉。因为“对方在思想观念上甚为敏感,达到智慧的顶端,故出现难以消解的嫌隙”。然而,这恰是梵乐希在人的理智上表达独特见解所需要的。于是,他安排了一系列采撷智果的“融合会面”,以“整步”满足他关于精神创造性统一,理智不能领悟本质的文学理论需求。按马利纳·朗德洛依的说法,“卡特琳屈从了这种吸血鬼行径(la vampirisation),任凭其吸食膏血”,大大充实了著名的梵氏学术日志(Carn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