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样的思维碰撞与你而言有多重要?
石黑:之前我说过——当时你问我小说家追求的真相是什么——我想到的是疑问:“难道你对此没有同感吗?这是我的看法。”我抛给别人的正是那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回答至关重要。
但是我并不会真的这样回应一众评论,说自己也许更应该这样写,或者那样写;我不会这样去做。
你知道,作品的概述对我来说和评价一样意味深长。他们在概述时,吸引我的是他们会如何总结小说,他们会觉得作品中哪些地方是核心内容,会如何解读某些东西,以及那一切是不是我期望强调的内容。
关于《长日将尽》,之前我会说我很抵触许多人从“日本性”来讨论我的作品,就好像是它们只有对痴迷于日本社会的人来说才有意义一样。我说的是早期作品。我创作的小说以和日本毫无关联的英国为背景——显然,那个决定也许受到了主流观点的影响,因为它们将我的作品看作是对日本社会的历史或者社会观念的阐释。
黄:这些累积下来的反馈促使你审视了作为作家的发展历程?
石黑:《长日将尽》证明,我回应的不是一两位对我应该如何写作指指点点的批评家。恰恰相反,总体而言我是有所不满的,因为人们在我早期的日本小说中过度搜寻信息,就好像我能和人类学家,或者记录日本文化的纪实作家那样,揭示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我觉得,可能我想表达的关于人类和人生更共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晦涩模糊。他们没有附和说“哦,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是说“这些日本人的想法真有意思啊”。
以日本为背景(在早期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评价,有点会让读者误解我的写作初衷。所以,那个例子说明作品的整体解读方式会左右我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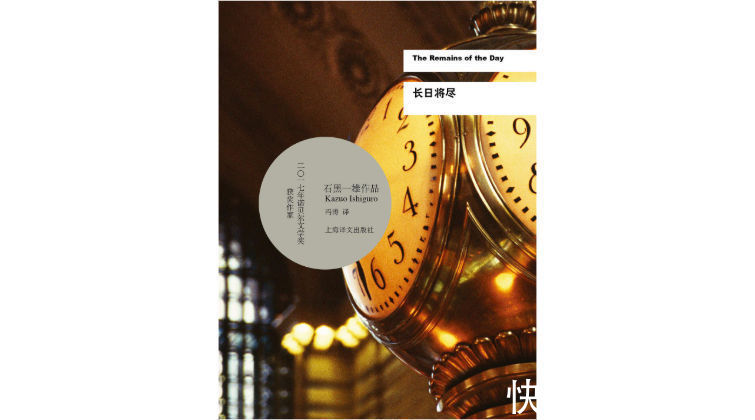
文章插图
《长日将尽》,作者:[英]石黑一雄,译者:冯涛,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5月
“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护的肥皂泡”
黄:在你的第五部小说《我辈孤雏》中,读者们不应该心存期待,认为他们会找到不曾在历史书中读到的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某种史实,是吧?
石黑:我认为是这样,他们找不到的。我所做的就是研读能找到的资料。有一两本书是我从珍本书店中淘来的,写于那个年代(三十年代),但是据我所知,书中没有说到不为人知的内容。里面提到了鸦片战争——这点人尽皆知——任何一本关于旧上海的书都会说到那些东西。
人们对上海津津乐道。也许我可以推荐这方面的许多好书,它们由训练有素的作者撰写,这些人追求的是研究艺术的精益求精,通过史料得出结论。
我把上海用作某种隐喻的场景。我是个靠不住的人;要是想了解历史细节,我是不会信任我这样的作家的。(笑)
黄:你能谈一谈《我辈孤雏》中的主旨或者母题的重要意义吗?诸如像“孤儿”,还有《长日将尽》联想到的“伟大”等主旨或主题。
石黑:关于孤儿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孤儿。当然,这部作品里,这些角色的确都是孤儿——他们的父母要么去世,要么失踪。这儿的孤儿状态有隐喻的意味。我希望在此处探讨的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护的肥皂泡,置身其中时我们对外界的凶险一无所知。
随着年纪渐长,我们走入更广阔的天地,懂得了命运多舛。有时候,这一过程温和而舒缓;有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则如晴天霹雳、急风骤雨。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生活在相对而言受到庇护的金钟罩里,活在受保护的童年里,他以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认为自己有了天大的麻烦,但其实不过是些小孩子们不要闯祸之类的小问题而已。
突然,他被扔进了成人的世界。问题变成了:当我们走入更险恶的世界,我们是否带着怀旧之情,带着曾几何时我们相信世界是个美好所在的回忆?也许,我们被大人们误导了,也许准确地说,我们被保护着免受这些厄运的侵袭。
之后我们走入了大千世界,发现这里有着污秽之事和棘手难题。有时,也许我们仍然残留着孩提时代的天真想法,并且有着想要重塑世界、拯救世界,想要让世界复原成孩提时代模样的冲动。
所以,最新的这部作品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猝不及防失去了童年天堂乐园的人。随着他的长大,也许是无意之间,他一直持有的人生宏伟目标就是要修复曾经的错误,这样他才可以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我所说的“孤儿”,指的是最广义上离开了我所说的保护我们的童年世界。
- 朵拉|2021年世界华文闪小说创作比赛线上颁奖
- 射雕英雄传|如果杨过是由郭靖亲自教授武艺,结果会怎样?
- 凡人修仙传|一本怪异的仙侠小说,差点把主角给写死,最终作者被“求着”封神
- 阳台上|闪小说Ⅰ欲罢不能
- 扎扎|波伏娃生前未公开小说遗作《形影不离》中文版出版
- 舞美|茅奖小说《主角》被陕西人艺搬上话剧舞台
- 故事|主角付出的代价越大,小说越吸引人
- 女儿|六年级女儿看的小说有性描写?妈妈慌了,网友:引导胜过屏蔽
- 春天里(小说)|为民 | 春天
- 骆儿|乡野小说《芝镇说》第二部7|是谁这么大胆,冲了俺的酒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