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蝎小猪
◎“谁叫他哥杀了人呢?”
《信》是东野第四度入围直木奖的作品(第129届直木奖,当时的最终获奖作是石田衣良的《4TEEN十四岁》和村山由佳的《星星舟》,皆已推出中文简体译本),日文原名《手紙》。该作先是在“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于2003年3月由每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三年后被搬上银幕,由偶像影星山田孝之、玉山铁二和泽尻英龙华担当主演。2006年底,与电影同期推出的文库本小说一个月内即热卖100万册,创下了出版方“文艺春秋”旗下图书销量突破百万的最快纪录。然而,这样的一本畅销作品,却几乎在2003年的诸个推理奖项和推理榜单中均未予列名,可见其推理成分之弱。
延伸开来说,东野入围直木奖的五部作品(依时间先后,分别是《秘密》、《白夜行》、《单恋》、《信》和《幻夜》,其中最不“推理”的就是读者诸君刚刚看完的这本《信》),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有所谓解谜的元素,也大抵是在揭示和剖析社会谜团吧。若非东野一向以推理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恐怕连“社会派”的标签都不会贴在本书上。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说,《信》已经跳出类型、流派的格局限制,兼得犯罪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之趣,是部集大成的作品。当然,这种“非类型化”,也正是东野圭吾自1990年的《宿命》以降、始终贯彻如一的创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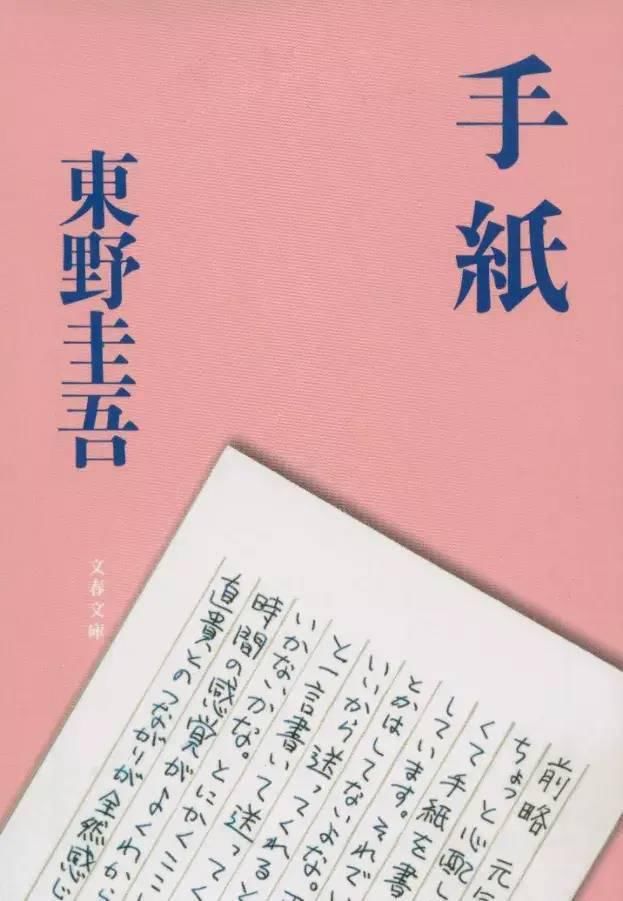
文章插图
(《信》日本文库版)
作为一名“创新型”作家,十分注重观察、体悟生活环境的东野圭吾,喜欢将自己的创作理念直接经由作品体现出来,这就造成了东野的作品不管是题材上、还是结构上,都深具创新实验性和时代前瞻性。关于这一点,东野曾如是阐述道:“每次更换领域的最大理由是我自己生厌,如果反复一直写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对许多事物都有兴趣,所以有时想写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我就是这样一路写下来的,所以每次都变成不同的作品。”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野的作品主题本本不同,比如揭示医疗黑幕的《宿命》、描述虐童事件的《我以前死去的家》、涉及文学界“影子作家”捉刀现象的《恶意》、讨论家庭伦理关系的《秘密》、试探日本升学教育问题和大人小孩之间冷淡疏离关系的《湖边凶杀案》、探究少年犯罪问题的《彷徨之刃》、牵涉诈骗犯罪行为的《流星之绊》等等,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而东野圭吾的这本《信》也是以具备社会意义的内容为作品主题的,此次他关注的是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
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对在父母死后相依为命的兄弟:哥哥武岛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的学费,铤而走险犯罪杀人;而弟弟武岛直贵,则不得不背负哥哥一手制造的精神债务,从此坠入社会歧视的轮回。“谁叫他哥杀了人呢?”这是直贵的一个同学在醉酒之后的无意之语。几乎每一位登场人物都必须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各自的言行。本作就是以加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为切入点的,这一特征倒是可以和同为东野作品的《彷徨之刃》(2004年)进行对应说明,因为后者正是从被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切入,牵扯出了问题多多的少年法。不管是《信》中的杀人犯弟弟,还是《刃》中的死者父亲,他们都在一桩并非当事人主观故意的罪行发生后,面对了人生道路的易辙,逐渐深陷被宿命无情嘲弄的泥淖而不得解脱。就是这样相对的两个“命运”,演绎出了两场典型的社会悲剧。东野圭吾用他那独特的笔触,将问题直接抛至读者面前,以淡于批判的口吻,诉说着我们所熟知却明显忽视了的哀伤。这种哀伤借着一封封轻质的信纸传达开来,那是“难以言喻”的沉重吗?
◎“歧视是理所当然的。”
在阅读《信》这本小说的过程中,笔者曾反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过歧视别人的经历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读者您是百年一遇的圣人,否则也应该和我一样吧。所歧视的对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属”这类接触机会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会是以下弱势群体当中的一种吧:下岗职工,无业游民,乞讨者,残疾人,农民工,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或特殊疾病患者(甚或只是病毒携带者),来自偏远贫穷地区的人,从事脏活、累活以及特定行业的服务人员,……还需要再罗列吗?这样的歧视对象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说,歧视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行为。所以《信》中一旦人们被告知刚志的事情,对方的反应便会像那个大胡子店长一样,“很快地就垒出一堵墙,只是不同的人垒出的墙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时候即使很难说达到可以称为“歧视”的那种严重程度,但至少区别于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谓“偏见”也还是有的吧。
- 23年婚姻输给23岁小三, 儿子自杀, 妻子: 我要让她不能怀孕
- 谢灵运《岁暮》,每到岁末,总要深深感慨一回
- 古代银票就一张纸,为何没人造假?不是古人不想,而是不能!
- 从历史看发展,说说为什么西方就不能向东方学习?
- 辛夷坞笔下的好小说,虐心不逊《十年》,娶了女主却不能爱
- 中国历史上最硬气的朝代,快灭亡时还打得周边外族不能自理
- 民间传说中,为什么神仙和凡人不能相恋原因很简单
- 总裁虐恋,“总裁,夫人已经抽了2000ml,不能再抽了!”他怒吼:继续抽
- 学文钞: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
- 《西游记》有两种动物不能写成妖!吴承恩表示不敢碰,让写也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