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
晓来谁把霜扑醉
——悼黄宗英
大众日报·新锐大众采访人员 逄春阶
十几年前,黄宗英在《新民晚报》写过一篇随笔叫《谁把霜扑醉》,开头写的是“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有人较真,说黄宗英记错了,应该是《西厢记》中的台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但我觉得黄宗英的“谁把霜扑醉”好,好就好在一个“扑”字。
12月14日凌晨,享年96岁的黄宗英去世了。看到这个沉重消息,我脑海里蹦出了五个字:谁把霜扑醉。

文章插图
我喜欢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模仿过她的报告文学,我喜欢她的灵动的语言和节奏,我喜欢她的报告文学的小说结构,无论是《大雁情》《星》《桔》,还是《小木屋》《美丽的眼睛》,差不多都是最多万把字的精短报告文学。但它们超过了现在动辄一大本的报告文学。我也学着她,尽量写短些。
最早接触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是在上海办的《文汇月刊》上,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先看到的是《他们三个》,反映上海“老三届”青年,命运坎坷,但矢志不渝,研究医学测量中出现的令人头疼的“0点漂移”难题,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医用自动永停滴定仪。术语的枯燥被黄宗英灵动的语言冲淡。我当时刚刚尝试写作,把黄宗英的人物描写、景物描写抄在本子上。“在他们最富于幻想地走向生活的当口,却满腔激情地接错了电源:闪光、雷霆、迷雾、风暴掀倒了这整整一代人。……”类似的充满张力的句子,感染了我,一直影响到现在。黄宗英给我的重要启发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报告文学可以掺入个人的感情,抒发个人的情绪,与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读黄宗英,我常常记得我的前辈赵鹤翔先生关于创作的叮咛:把灯挑亮,让血肉鲜活灵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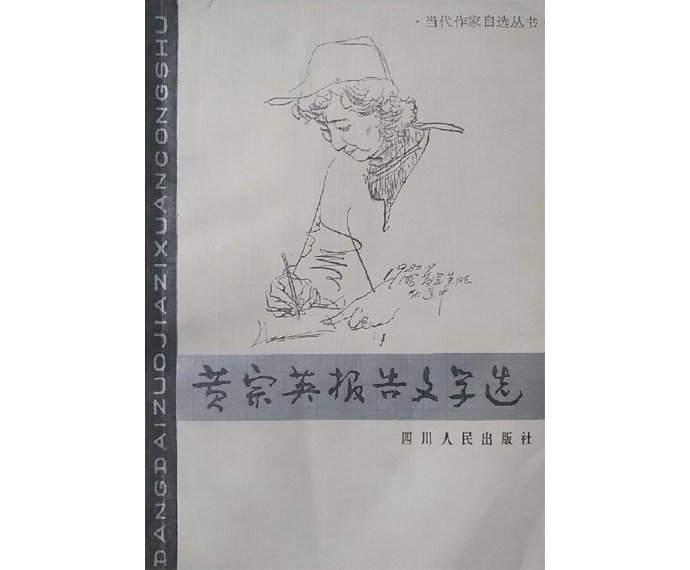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当然,影响我最大的是黄宗英的关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谈《与人物共命运》,下面的话,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提醒:“如果把笔者的感情比做一团带电的云,能击撞出雷电的,就意料不到的落在了我的稿纸上。不是我选题材,是题材撞上了我。”“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活着,我是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一个姐妹、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阿姨、一个长者、一个晚辈、一个知心朋友。我应该随时随地想到自己应该做什么——在生活中以自己的身心去写;而后,才谈得上在稿纸上写。” “写普通人,普通人总是绝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一个。”“写正在行进的人们。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不重在写一个人做成了什么;而重在写他是什么样的人。报告文学不能等同于英雄榜、劳模榜。有所追求的人们,我愿之同行。强者,携着我;弱者,我挽着。我更喜欢强者,由于我软弱,我需要力量。……我不纯客观地去描写人物、报告事件,而是与我描写的人物同甘苦、共命运去迎艰涉险,痛醉黄龙。”这些话,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引过来,一点点地践行之。普通人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来的,每一天都不虚度。视自己的职业为神圣,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神圣,光泽在普通人身上,我必须盯紧他们,留心,耐烦。

文章插图
1956年,黄宗英与孙道临等联合出演了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电影《家》,在其中扮演梅表姐。
黄宗英的哥哥,著名作家黄宗江曾说过:“我不能灰色地活着,我不能黑色地活着,我要亮色地活着。”而黄宗英就是一直活在亮色中。她在《谁把霜扑醉》中有这样一段写到她的先生赵丹:“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
